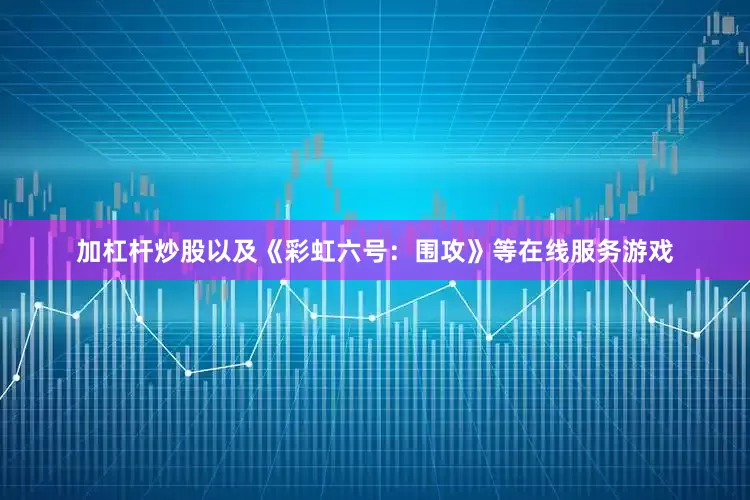在东北地方志的星空中,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与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是两枚独特的星星。它们不仅是打牲乌拉地区最早的专志与续编,更以“原始档案+乡土叙事”的双重视角,为清代东北史、满族史乃至边疆治理史提供了鲜活的注脚,为吉林省及东北地方志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。借《吉林全书》结集出版之机,再度以全貌问世。
打牲乌拉,清代皇室的“贡牲基地”,以采捕东珠、貂皮等贡品闻名。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成书于光绪十年(1884),由打牲乌拉总管云生主持编纂,四册六卷的篇幅里,几乎是一部“乌拉地方档案大全”:上至皇帝谕旨、内务府指令,下至牲丁数目、贡山章程,甚至俄国分界、海参崴驻防等边疆要闻,皆以原始文书形式留存。书中记载的“清代官僚剥削牲丁”“乌拉兵镇压太平天国”等细节,更以第一手材料撕开了“皇家贡地”的神秘面纱——这里不仅是物产的输出地,更是清代政治网络中的一个“神经末梢”,其兴衰与中央集权、边疆危机紧密相连。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卷三因长期散藏于打牲乌拉总管后裔赵东升家中,此次影印出版填补了国内馆藏空白。这种“民间流散+官方整理”的出版历程,本身就是一段“古籍回家”的传奇,更凸显其版本价值——它不仅是文献,更是一段文化传承的见证。
若说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是“官方视角的宏大叙事”,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(光绪十七年,1891)则是“在地视角的细节补充”。作为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的续编,它虽仅一册八十五页,却以“统颁项目”的体例,将内容延伸至金石碑文、户口田赋、名宦人物等更贴近民生的领域。例如,其对“城池津梁”的记录,不仅补全了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未载的地理细节,更通过“户口田赋”的数据,勾勒出乌拉地区的经济生态;“名宦人物”部分则以具体人物为线索,串联起地方治理的脉络。这种“广而细”的叙事,让“打牲乌拉”从“贡地”升维为一个有血有肉的“地方社会”。
两书的关系,恰如“同源分流”: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重“史”,以档案为骨;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重“志”,以细节为肉。时间上,前者成于1884年,后者晚七年;内容上,前者“广而粗”,后者“狭而精”,二者互相印证,共同编织出打牲乌拉的立体图景。
当然,作为清代官修志书,两书亦有局限。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因大量直接摘录档案,语言未经修饰,可读性稍弱;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则因类目庞杂而内容略显单薄。但这些“缺陷”恰恰是其价值所在——未经修饰的原始性,反而规避了后世编纂的“主观过滤”;类目虽多却“有闻必录”,保留了清代乡土志的真实体例。
更重要的是,它们为学界打开了多把钥匙:研究清史者,可从中窥见内务府与地方的互动;研究满族史者,能看到满族对东北的开发贡献;研究边疆史者,能捕捉到俄国侵华、东海防守的细节;甚至研究地方志编纂史者,亦可通过两书的“续编关系”,观察清代地方修志的官方导向与实践逻辑。
从《打牲乌拉志典全书》到《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》,打牲乌拉的故事从未局限于“贡牲”二字。它们既是一部“地方志”,更是一面“国史镜”——通过乌拉河畔的采捕声、牲丁的赋税单、边防守军的调令,我们看到的是清代国家治理的微观运作,是东北边疆从“封禁”到“开发”的历史转折,更是一方水土与整个帝国的命运交织。
(作者:姜沐雨)
广瑞网-广瑞网官网-最新上线配资app-股票配资服务中心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炒股杠杆配资从侧面证实了央企介入李家港口交易属实
- 下一篇:没有了